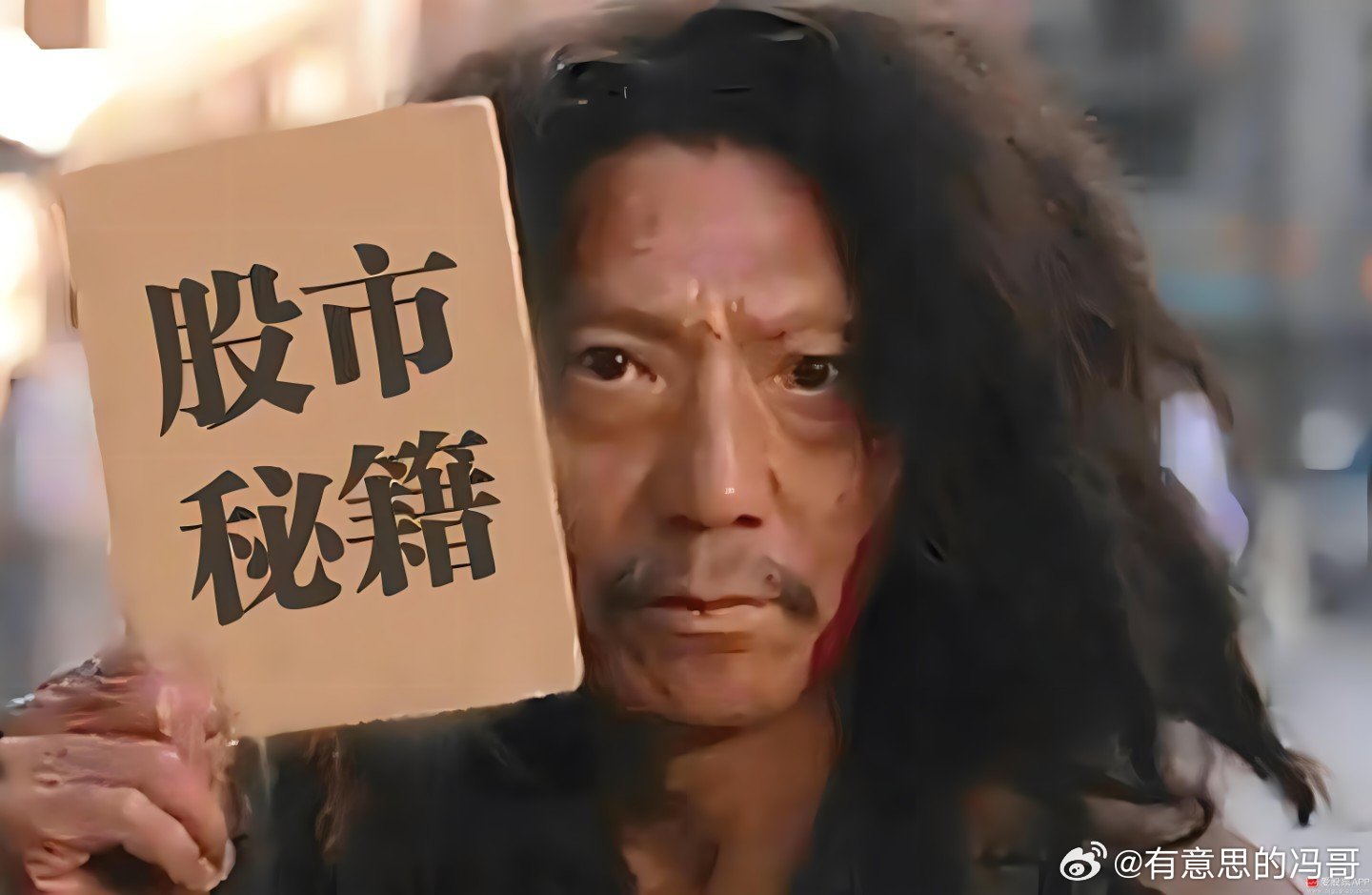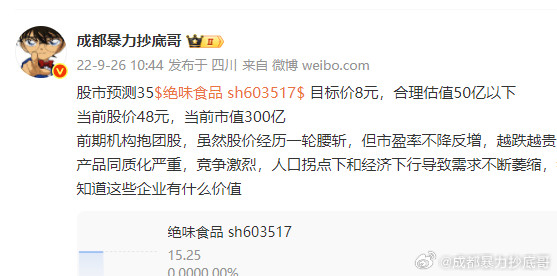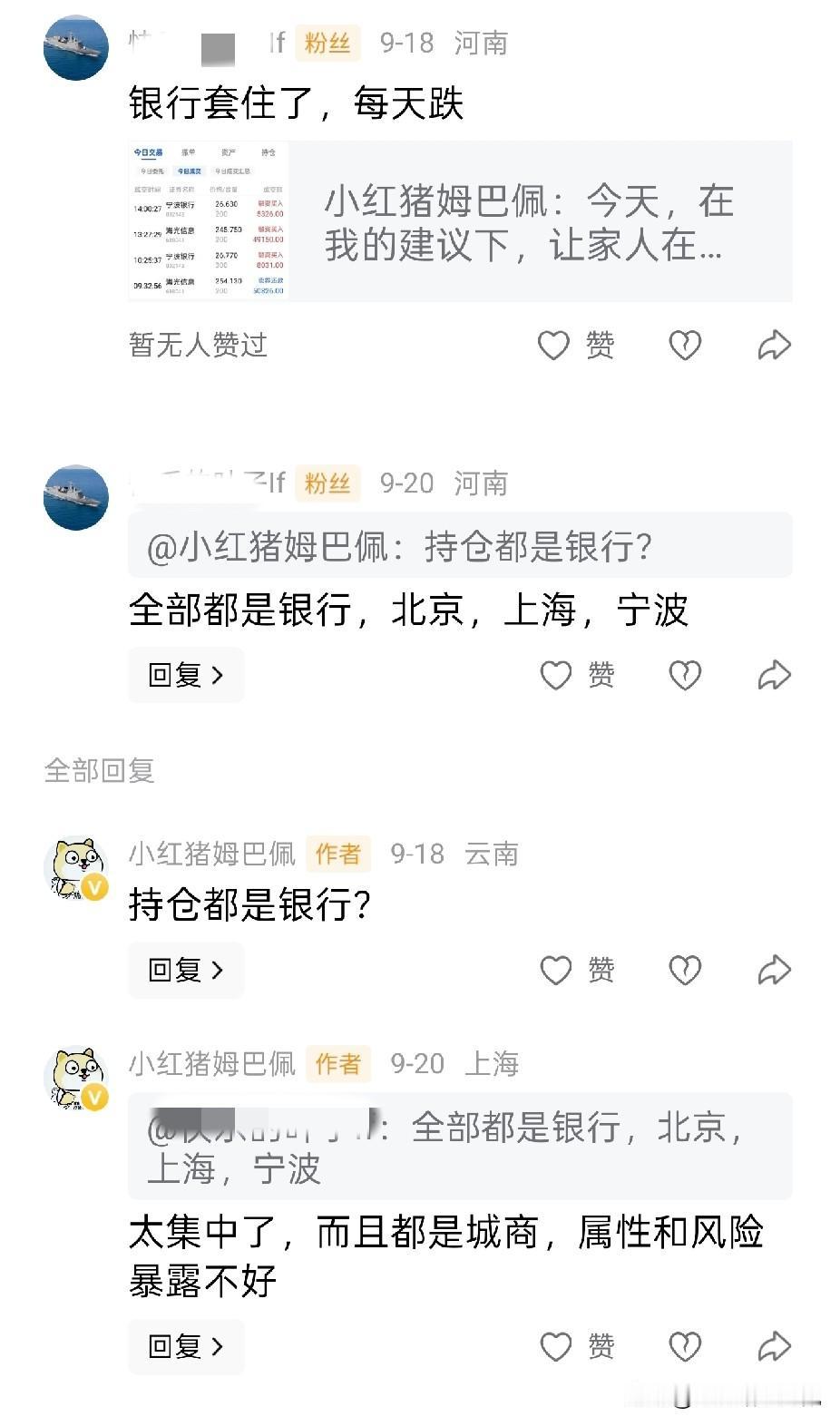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当嫌疑人一言不发,司法机关该如何办案?近期,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办理的又一起“零口供”内幕交易案尘埃落定。
嫌疑人坚称自己与家人买入股票时对内幕消息不知情。但检察官找到身处海外的证人获取证言,从而证实嫌疑人在一场饭局上与他人谈论内幕消息,最终嫌疑人与两名家人以内幕交易共犯的身份定罪。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动作,往往会给股价带来重大影响,也通常被视为内幕信息。在巨额收益的诱惑下,部分掌握内幕信息的高管等人,违规将敏感信息传递给亲友,让亲友买入股票。案发后,为避免连累泄密者,亲友在面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时,往往守口如瓶。
如何将泄密者绳之以法,成为司法机关面临的难题。作为全国七个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之一,市检三分院近年来通过梳理交易痕迹、比对通话记录,在多起“零口供”案件中找到突破口。

检察官在讨论案情
案件1:一个电话号码暴露的秘密
2017年6月,某上市公司公告称,该公司控股股东某公司将与另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合并重组,并宣布停牌。就在股票停牌前一周,河北夫妻王瑞明、陈佳先后动用10个证券账户,调集1.19亿元资金大量买入这家上市公司股票。
由于处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这笔异常交易立即引起监管关注。2019年底,证监会对王瑞明夫妻的内幕交易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同时有关部门也发现,王瑞明的堂兄王劲松,便是这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某公司的高管,还是并购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进一步调查发现,王瑞明夫妇的交易时间,和重组的重要时点几乎重合:
2017年5月25日,公司开完重组工作会,当天下午,王瑞明连续给陈佳打了多个电话,陈佳随即调集200多万元进场买股票。第二天,陈佳再次大手笔买进股票,成交金额高达1.07亿元。
6月2日,公司召开党组会确定于6月5日停牌,当天也是股票停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陈佳又追加1000万元购买股票。
此外,夫妻俩和王劲松有多个电话来往。一切迹象显示,夫妻俩极有可能是从王劲松处获得内幕信息才买入股票,但王瑞明、陈佳坚称买股是基于“个人判断”,双方之间的电话联系则是在商量已故亲属的迁坟事宜。
案件线索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后,承办检察官认为,王瑞明夫妻的说辞存在诸多不合理。“首先,在用来买股票的资金中,银行借款规模高达8000余万元;其次,第一笔下单没有成交的情况下,他们立刻撤单,加价挂单。并且两个人之前都没有买过股票的经历。”市检三分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黎涛介绍。
不过,仅凭这些迹象还不足以认定王劲松泄露内幕消息。6月2日之前的一段时间,王瑞明夫妻似乎没有和王劲松有过联系;而王瑞明也坚称,5月25日的电话联系是因为商量迁坟事宜。
如何找到关键证据?检察人员尝试从大量的通话记录中寻找突破口。在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多月的上千条通话记录中,6月1日的两条通话记录引起检察官注意。当天,身在河北的王瑞明曾经和一个010区号的北京电话有过两次通话。
这究竟是谁的电话?“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放在网上检索,发现这个号码属于王劲松所在公司的内部酒店。”黎涛回忆。真相逐渐明晰,就在6月1日,作为公司高管的王劲松曾参与并购重组相关文件的起草,而起草地点就在这家酒店。
据此,检察人员梳理出内幕交易的时间和双方联络的时间高度吻合。“法庭上,我们对王劲松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教育转化。”面对双方通联的证据,一直没有松口的王劲松终于认罪认罚,并写下悔过书。原来,作为起草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会议结束后,悄悄用酒店电话给堂弟打电话。“攻守同盟”至此被瓦解,堂弟夫妻也相继认罪认罚。最终王瑞明夫妻因犯内幕交易罪被判刑,王劲松因犯泄露内幕信息罪获刑。
“对泄密人员的定罪,一直是难点。之所以我们敢提起公诉,正是因为挖到了他们传递信息的隐蔽途径。”黎涛介绍。
案件2:一句“别问了”背后的暗示
在另一宗案件中,检察机关同样通过细致梳理交易习惯和交流细节,揭开了隐蔽的泄密方式。
2018年3月初,一家陷入经营压力的上市医疗公司委托某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一揽子综合服务,以此化解债务危机。消息一旦被披露,势必将影响股价。
就在信息尚未公开的敏感期内,当年9月,老股民张利民动用近2000万元买入该公司股票。一些细节显示,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投资。该医疗公司刚刚被ST(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等异常情况时,证券交易所发出风险警示),ST股票高风险高回报,但张利民在之前4年内没有交易过ST股票。
这一笔敏感交易未能逃脱监管,张利民随即被证监会行政处罚。在买入医疗公司股票前,张利民仅和一名叫陈志文的人有过密切联系。陈志文是资管公司高管,全程参与并担任该项目负责人,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就在8月中旬,张利民和陈志文打了一通电话之后,张利民大量买入这只ST医疗股票。
2024年,该案被移送市检三分院审查起诉。因时间久远,陈志文和张利民对案发时的交往细节已记忆模糊,供述闪烁反复。在被检察官询问时,张利民只说,自己和陈志文有多年私交,存在长期业务合作。2018年,两人在多次见面、电话联系中,都曾讨论过上市医疗公司的不良债务问题,这使得张利民感觉到——陈志文所在的资管公司应该对做医疗公司的不良资产业务比较感兴趣,甚至他还曾直接询问资管公司是否要做医疗公司这项业务。“通过和陈志文的交谈,我更加确定了这只票肯定要买,未来肯定有利好消息。”张利民在一次供述中承认。
“这让我们坚信,陈志文肯定跟他说了些什么。”检察官王亚喆表示。但面对检察机关的问询,陈志文却坚称,自己从未向张利民透露该上市公司重组一事。经过检察官的一遍遍追问,陈志文透露一个细节:2018年8月的一通电话中,张利民再次刺探医疗公司重组一事,陈志文说“别问了,我不知道”,随后张利民便挂断电话,很少与陈志文再联系。
“以往过程中,陈志文和张利民谈及业务问题,回答都很专业,这次陈志文用‘别问了’这样含糊的方式回复,二人已经心照不宣,此后骤然减少联系、保持距离,反映了二人对传递内幕信息刻意回避的心态。”王亚喆介绍,据此,检察机关认为陈志文面对张利民的主动刺探行为,采取暗示方式泄露内幕信息,应当以泄露内幕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陈志文和张利民分别因犯泄露内幕信息罪、内幕交易罪而获刑。
突破:如何找出内幕交易背后的证据链
给泄露内幕信息的人员定罪,一直是司法机关办案的难题。内幕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往往并非高管等内幕知情人,而是其亲友、配偶。由于传递信息的方式极为隐蔽——可能是一通电话,也可能是一场饭局——通常不留直接证据。
夫妻一方掌握内幕信息、另一方下单交易的情形,认定犯罪相对容易,因为夫妻双方天然存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关系。而涉及亲友、朋友等非夫妻关系时,对泄露者的犯罪认定就困难得多。
“嫌疑人常常提前销毁联络证据,面对质疑,往往坚称电话是聊家事,买股是出于个人判断。”黎涛介绍。因此,即便证监部门监测到异常交易,多数时候只能追究交易一方的责任。要证明内幕信息知情人“故意泄露”,则尤为艰难。毕竟,有时“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时可能只是不小心说漏了嘴。
在此情形下,检察人员必须在细微的痕迹中寻找突破口:交易习惯是否异常,资金调集是否急迫,通话记录是否与敏感时点吻合。很多工作无法依赖技术手段,只能靠人工“笨办法”——调取几个月的交易和通话记录,逐条比对,甚至尝试在通讯社交软件上添加手机号,以确认背后身份。
“通过比对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交易时间、资金调度时间与双方联络时间,最终的目的,便是拼接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锁定内幕信息泄露者。”黎涛告诉记者。
建议:多个监管部门加强信息共享
自2022年集中管辖北京市证券期货犯罪案件以来,市检三分院案件办理数量逐年递增。2024年受理批捕和起诉案件数量同比增长38%、35%。
案件类型上,除内幕交易类案件外,市检三分院也在财务造假、操纵市场案件中深挖线索,从严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以某知名影视公司财务造假案为例,除追诉上市公司实控人和高管外,市检三分院还将配合造假的第三方公司人员、中介机构一并追责,实现全链条打击。
在依法从严打击内幕交易的同时,如何从源头防范问题,同样是司法机关关注的重点。市检三分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庞一然认为,部分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守法意识仍有待提升,很多人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风险知之甚少,有些人在行政调查结束移送司法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已然触犯了刑法。
此外,部分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短板,内控体系形同虚设,内幕信息管理和业绩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个别中介组织本应在职责范围内保持专业性和独立性,却未能坚守应有的职业操守与道德底线,沦为造假“帮凶”;同时,证券执法司法协作配合仍需进一步完善强化。
“只有加大对重点领域证券期货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持续高压震慑,才能有效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净化资本市场生态,提升投资者信心,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市检三分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邬娟介绍,该院将继续完善行刑双向衔接机制,推动证券执法与司法协作,同时还将不断健全完善证监部门与检察、侦查机关的共商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办案协作。
(本文中除检察官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