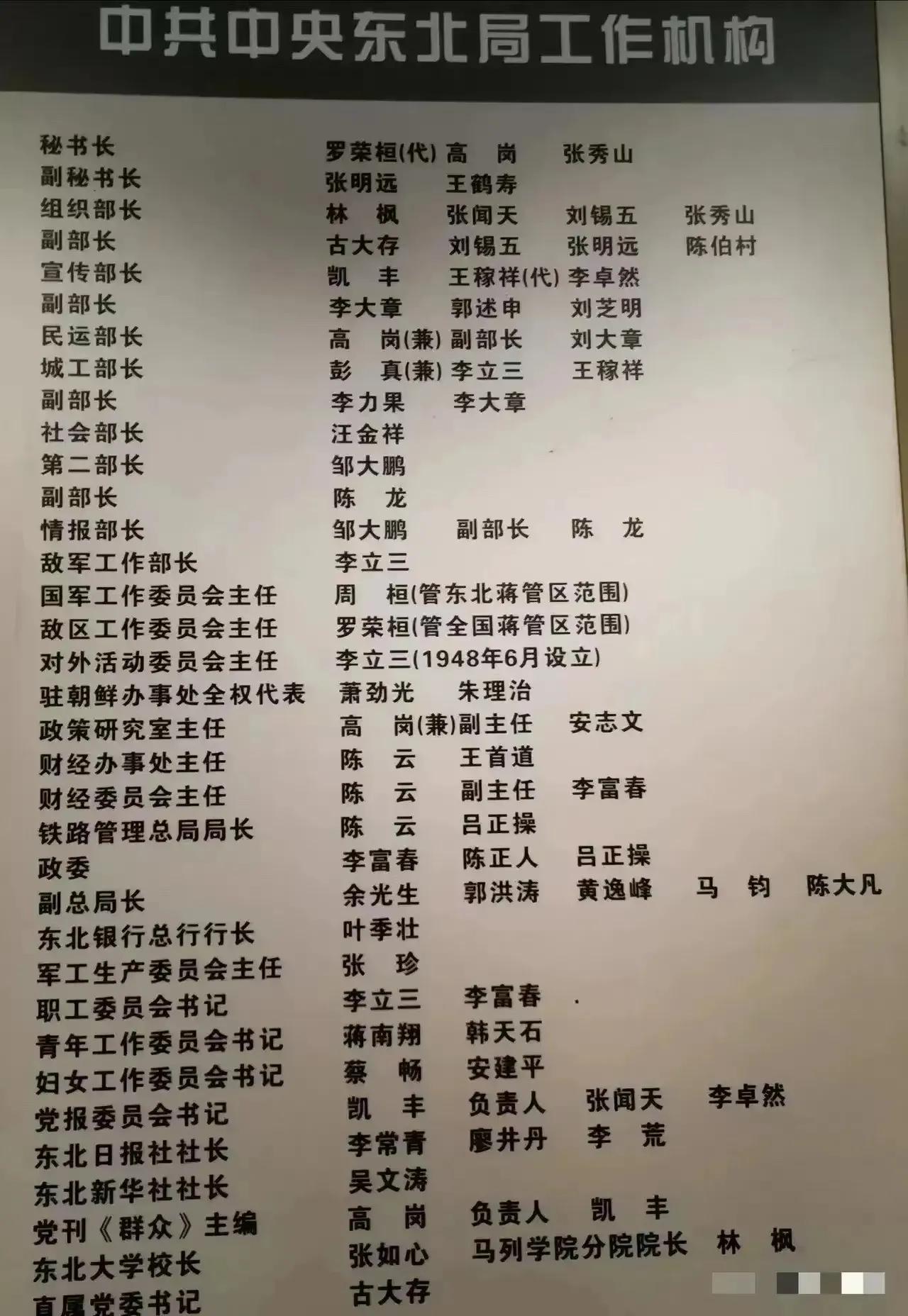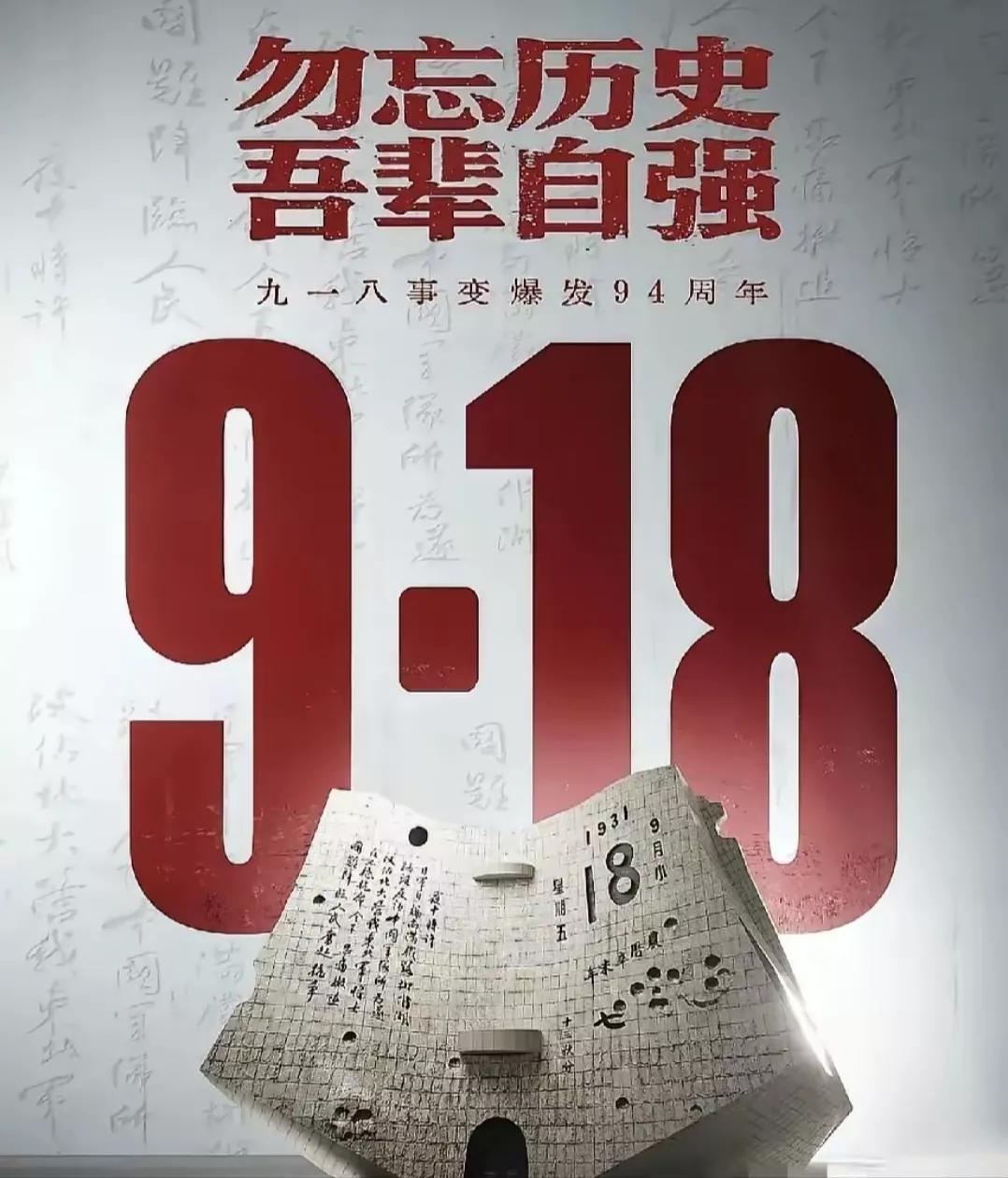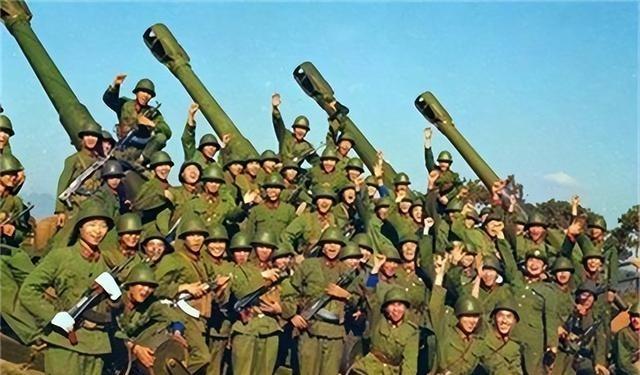赴死之前,他回头望了望家乡。 请大家记住照片中的人,他叫——陈阿生。当兵之前是一个走街串户的小货郎,淞沪会战前夕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88军,半月后,在防守罗店外围的小阵地中,陈阿生跟他的战友坚守了三天三夜,最后被日寇的坦克大炮突破阵地,战士们与日寇展开肉搏,全部壮烈牺牲。 —— 照片里的他,咧着嘴,牙有点黄,像刚把最后一颗麦芽糖塞给弄堂尽头的小崽子。谁会把这样一张脸跟“壮烈”俩字搁一块儿?可偏偏,就是这么个挑扁担的小货郎,把糖担子一扔,跟着招兵的老李头走了。那天傍晚,弄堂口的梧桐叶子正往下掉,他回头冲邻居喊:“糖罐子搁阿娣家,回头我请你们吃喜糖!”结果,糖罐子至今还在阿娣家的灶台上,盖儿生了锈。 88军的军装大了一号,袖子卷三圈还遮手指。班长笑他:“小扁担,你拿得动枪吗?”他把枪往肩上一甩,枪带勒得锁骨生疼,嘴里却硬气:“我挑过两百斤的麦芽糖,这铁疙瘩算个屁!”半月后,他们连被拉到罗店外的一片棉花地,地里的棉桃刚裂口,白絮被炮声震得漫天飞,像提前下了场雪。 头天夜里,日军炮群敲鼓似的轰了仨钟头,战壕里的土蹦起来又落回去,把人都埋成土俑。陈阿生半截身子被埋,嘴里全是泥,吐一口,带两颗牙。他旁边的新兵蛋子才十七,哭腔都岔了:“哥,我想回家看花灯。”陈阿生把兜里最后一块麦芽糖掰两半,大的那块塞过去:“含着,甜了就听不见炮。”第二天,十七岁的娃把糖纸贴在胸口,胸口被弹片撕开的时候,糖纸还黏着,血浸过去,像裹了层红糖浆。 第三天傍晚,坦克履带“咔啦啦”碾过来,钢板上贴着膏药旗,红得像烧红的烙铁。子弹打上去,蹦出火星,跳弹把自个人的脑袋削掉半个。陈阿生看着那半截脑袋滚到脚边,嘴还在动,好像喊娘。他红了眼,把集束手榴弹绑身上,爬出战壕那一刻,棉絮落在脸上,软绵绵的,像小时候娘给缝的棉袄。他想起离家那天,娘追出来塞给他两个煮鸡蛋,还热乎。他喊了句啥?没人听清,炮声太大,可能喊的是“娘”,也可能是“阿娣”。 爆炸响完,坦克停了,膏药旗烧成一团黑蝴蝶。阵地保住了?没人说得清,反正后来援军找到这儿,只剩一堆烂棉絮、碎骨头和半块印着“陈”字的布条。布条被血泡得发硬,风一吹,啪嗒啪嗒打坦克的铁壳,像货郎摇的拨浪鼓。 故事要是到这儿就结束,顶多算“又死一个”。可偏偏,阿娣没嫁,守着糖罐子过了八十多个秋天。每年淞沪会战那天,她把罐子擦得锃亮,摆门口,里头空空的,却像盛满整条弄堂的甜味。小孩子们问:“奶奶,这罐给谁留?”她咧开没牙的嘴:“给一傻子,他说回来请吃喜糖。” 后来,镇上新修了广场,立了块大碑,刻着“罗店英烈”。碑前面总摆着各种糖,软的硬的,带芝麻的不带芝麻的。城管来收,第二天又摆满,谁摆的?没人承认。只有半夜扫大街的老头看见,一个佝偻背影把糖排得整整齐齐,临走还拍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笑得牙有点黄。 有人说,陈阿生傻,一条命换块破地,值吗?要是他肯蹲战壕里装死,兴许能回来接着挑扁担,娶阿娣,生一堆娃,晚上给娃们分麦芽糖,糖纸攒多了还能糊风筝。可他就是站起来了,腰杆笔直,像根扁担,挑起的不是糖,是后面那十七岁娃的命,是弄堂里还没睡醒的黎明。 我外婆家离罗店不过二十里。小时候她哄我睡觉,不唱摇篮曲,就讲“糖罐子的故事”。我嫌烦,说:“都老黄历了,还提它干嘛?”外婆拿蒲扇敲我脑门:“你小子现在能躺着挑雪糕,就因为有人替你站起来了。”长大后,我跑去罗店,棉花地早变工业园,坦克履带印找不到,只剩碑前黏糊糊的糖,被太阳晒化,蚂蚁排成队,像小小援军。我蹲那儿,忽然明白:所谓“壮烈”,不是碑上金漆大字,是有人把生路让给你,自己走进糖纸一样薄的命运。 所以,别急着问值不值。先想想,如果那天换你,你肯不肯把最后一块糖掰给别人,然后笑着往火里跳?肯了,你就懂陈阿生;不肯,也正常,毕竟甜味谁不爱。可正因为大多数人舍不得,他才显得像根骨头,卡在历史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提醒每一代人:别光记得甜,忘了甜从哪儿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