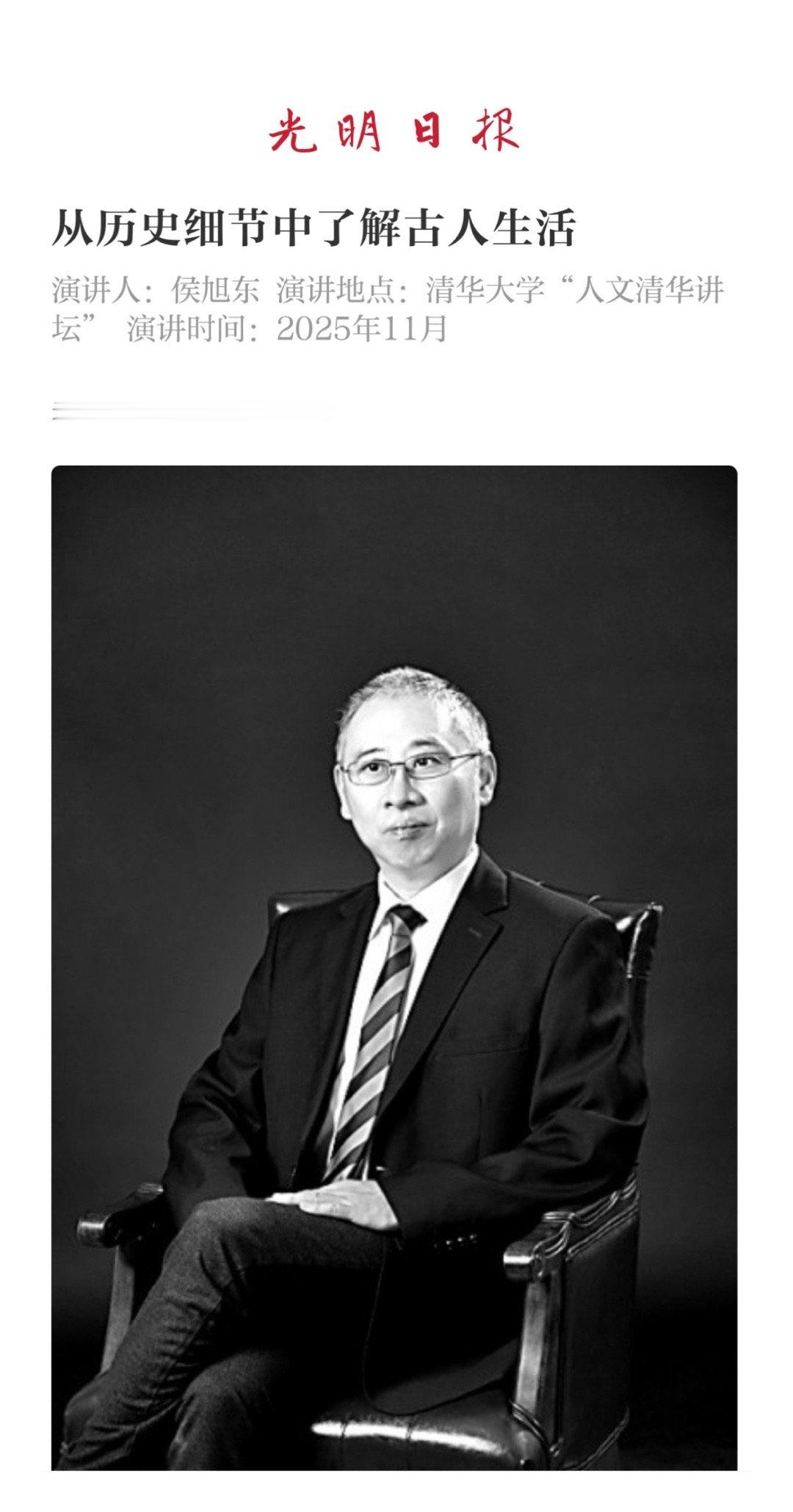【从历史细节中了解古人生活 ——侯旭东教授在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的演讲 (续) 】 (光明日报 2025-11-29 07:53 ) * 侯旭东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秦汉三国文书简牍、早期中国国家形态与运行机制等。著有《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 [ 简牍深处普通人留下的历史印记 ] (续前:网页链接 ) 有日本学者根据师饶的日记,绘制过一张元延二年师饶郡外出差的行动地图:这一年他共外出六次,去过东北方向的琅琊国,也去过西南方向的楚国(楚国都城彭城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师饶曾经多次出差至彭城,且住宿天数亦多,最长一次住了将近20天,和楚王有很秘密的往来。遗憾的是,师饶在日记中并未记录他这期间具体做了什么,推测是在替郡守执行任务。按当时规定,郡守不能随便出辖境,所以他只能派亲信联络沟通,师饶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在师饶记录的元延二年诸多历史细节基础上,我们再对这一年的整个西汉王朝进行审视。在《汉书・成帝纪》的记载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元延二年相关内容一共只有四条,其中三条是皇帝行幸各地祭祀或狩猎,还有一条是分封宗室为诸侯王。这一年没有灾荒,也没有地方动乱。以往我们阅读正史,读到类似的天下承平记录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皇帝,诸如成帝、元帝、武帝等等,而通过简牍资料,我们还看到了这些记录背后忙碌的师饶等众多小吏。类似师饶这样的小吏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西汉王朝治下当时和东海郡一样的郡国有103个,县级单位有1587个,小吏总数超过11万。而且11万只是一年的数字,如果一位小吏任职的时间以20年计,整个西汉二百多年的小吏人数应该超过110万。 师饶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在西汉王朝的东端,靠近东海。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一位小吏,则工作在西汉王朝的西端——敦煌郡。大家都知道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还在当地发现了悬泉置遗址。悬泉置是汉代打通河西走廊后,修建道路和交通保障设施时建立的,在这里出土了3万多枚汉简,记录了当时中西交通的珍贵信息。 我们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份记录《鸡出入簿》谈起。这份《鸡出入簿》的时间是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出鸡”记录的是消费吃鸡的情况,“入鸡”记录的是鸡的来源,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份簿册的全部内容。 乍一看去,这样的记录是琐碎且无聊的。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隐藏的历史细节。首先,这份记录是谁做的?是里面提到的“时”,他当时的职务是厨啬夫,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总厨。簿册里面记录了哪些人消费了鸡肉呢?有丞相史、大司农卒史、太医、使者,这些人均来自长安,记录最后注明“东”,意即这些人吃完鸡后向东而去,这说明他们此行是完成西行使命后东返长安。记录里还提到“往来再食”,就是说有些人往返都会在这里消费。除了中央官吏,还有郡级或州级官吏,也都是鸡肉的消费者。而所供鸡肉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悬泉置购买的,另一类是各县提供的。记录里还写明了鸡的价格:“一双鸡80钱。”即一只鸡40钱。 从物价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元康四年西汉大丰收,谷价便宜,一斛谷物只值5钱。一只鸡40钱相当于8斛谷物,汉代一斛谷物约等于今天60斤,8斛即480斤谷物。这样来看,当时一只鸡相当于480斤谷物,可谓非常昂贵。所以只有行经悬泉置的西汉朝廷中枢、郡级和州级官员才能享用鸡肉,而普通官吏每顿饭只能食用三升米或三升粟。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从《鸡出入簿》中发现什么?现在我们如果走汉代人路过悬泉置的这条对应路线,大致是从西安到敦煌共计1693公里,步行大概要394小时,按每天10小时步行算共需40天,沿途均需要食宿。现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宾馆、饭店,但2000年前的汉代,这条路线上只有官方设置的传舍等机构提供食宿。今天的我们只看到悬泉置遗址,但在西汉王朝治下,当时的全国交通线上有很多这样的设施,构成了一张西汉交通网络。我曾经做过统计,当时西汉治下这样的交通设施共有2057个,每个都要承担接待任务。除了《鸡出入簿》记录的鸡肉消耗之外,往来人员的食宿、马匹、车辆等都需要记录。当时无数个像“时”一样的小吏,每天都进行接待、记录、统计的工作。西汉末年,王朝每年要消费约15.2万只鸡;消耗的粮食更多,不仅供往来官吏食用,还要喂大量马匹,一年共消耗240万斛,相当于当时全国田租收入的2.9%,也相当于运到长安漕粮的60%,总体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从时间轴来看,这样的交通机构不只存在于汉代,后世历朝历代都有,唐代称之为馆驿,宋代叫驿馆或递铺,元代叫站赤,明清叫驿站。有学者曾推算,唐代和清代这类机构的年花费,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0%。正是这些机构支撑着从汉到清诸统一王朝的交通,这些机构中曾有千千万万“时”这样的普通小吏的身影。 除了师饶和“时”,我们在简牍里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普通人历史印记:湖北云梦睡虎地西汉简里,有一批工作日志,其主人叫“越人”,生活在西汉前期文帝时期,墓里出土了他14年的日记,记录了他这些年的行踪;睡虎地还出土过更有名的一批秦简,主人叫喜,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根据他墓里的头骨复原了形象,我们得以看到2000年前这位秦代县吏的模样。 当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轨迹在我们面前日益清晰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历史研究观念的发展、没有新史料的发现,我们可能无法看到这些普通人物的历史印记。 [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形成 ] 在发掘出历史中不易察觉的细节之后,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历史细节关乎着“历史的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的可能性”?清华大学历史系前辈学人、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还有更多未实现的可能。我们的历史研究应从“历史现实性”“历史事实”往前一步,研究“历史可能性”,如此研究对象能大幅扩大。用他的话来说“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 以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为例。我们何时进入农耕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栽培稻距今1万年,粟栽培约8000年。按常规认知,有观点认为那时已进入农耕社会。此说有一定道理,从考古发现来看,不同时期稻田、麦田遗址均有发现,比如汉代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出土了田垄遗迹与农民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篇论文还复原了汉代农舍。但是,当时这样的发达农耕区是否普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秦代律令(秦始皇统一前后颁布)记载:“新黔首不勉田作,缮室屋。”“新黔首”指东方六国百姓,指他们中不少人不努力种地、不愿修房子,流动性强。再看汉代,虽发现了农田遗址,但《汉书・地理志》记载,除关中、梁宋地区农业发达外,很多地区的农耕水平尚不够发达。班固描述:天水、陇西地区“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地区“好射猎”(这两地靠近游牧区,受游牧文化影响);颍川、南阳地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百姓“好商贾渔猎”,农耕同样不发达。这些表述提醒我们,至西汉时期,即便在相对发达的北方地区,农耕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当时农耕更为落后的江南地区。 我们以当时的渤海郡为例。此地是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如今农耕发达,但在西汉中期,渤海郡当地人并不重耕种,依赖渔盐、偏好经商。西汉宣帝时期渤海郡太守龚遂推行“劝课农桑”,要求百姓种树、种菜、养鸡养猪,督促务农,百姓不得不卖刀剑买牛犊从事牛耕,史载当地风俗很快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否真的很快实现,仍可探讨。再如东汉末年的郑浑,他曾任下蔡县(今安徽凤台)、邵陵县(今河南郾城,属颍川郡)县令。彼时南阳、颍川地区人仍不喜欢农耕,偏好渔猎,不重产业,风气持续较久。郑浑任内要求百姓种地、开垦稻田,还鼓励生育。 龚遂、郑浑只是当时众多推广农耕的地方官代表。正是在无数人的持续努力之下,约在7世纪初的唐朝初年,古代农耕社会才最终形成。唐朝初年编写的《隋书・地理志》描述各地风土,多数州均提到百姓“务于农事”“尚稼穑”“重农桑”等,用词略有差异,核心意思相同,和《汉书·地理志》相比,农耕已成燎原之势,南方多地也变为农业发达区。这一过程从战国到唐初,历经约1000年时间。这说明中国农耕社会形成并非单线、必然,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如若当年是齐国而非秦国统一全国,如若后续历朝无“劝农”政策,如若地方官吏不持续督促,或难有此局面。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发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历史细节与“历史的可能性”之间关系更加重视。 [ 小 结 ]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历史细节的多角度发掘与审视。我们所说的“历史”,既指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也指对历史的记录与研究。历史与今昔紧密相连,个人的“小历史”终将汇聚成时代的“大历史”。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进一步发掘,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用历史来映照当下、探索未来,我们从历史与历史学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 (本文系2025年11月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文稿整理修订而成,原文稿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刘师昭整理) 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