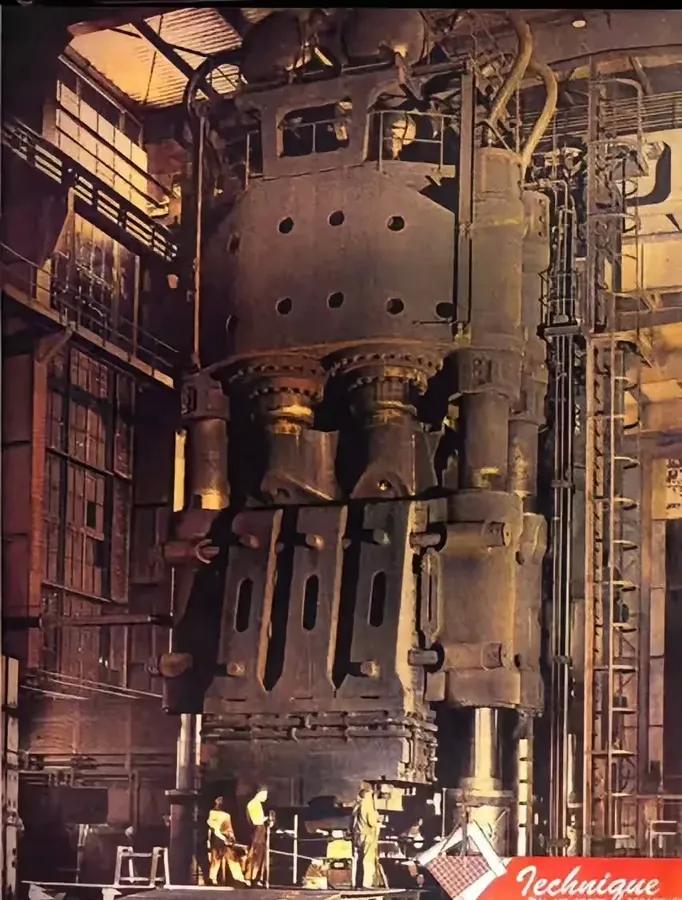1904年,通房丫李氏,站通房丫李氏,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长达33年。这日,她正在盛饭。谁知,管家突然冲进来高喊了一句,她手一歪,啪地一声碗摔落地面碎了一地。正妻刚打算开口斥责,丈夫却开怀大笑:“坐下,一同用膳!” 李氏僵在原地,指尖的温度瞬间褪去,满手都是冷汗。瓷碗碎裂的脆响在堂屋回荡,像砸在她心上,震得她头晕目眩。她今年四十八岁,十二岁那年家里遭了蝗灾,爹娘把她卖进沈家当丫鬟,十五岁被抬为通房,这一伺候,就是三十三年。三十三年里,她每日天不亮就起身,洒扫庭院、伺候主家梳洗,三餐时站在桌旁布菜添饭,夜里守在外间,随时等候吩咐。正妻王氏性子不算刻薄,却也从未给过她好脸色,丈夫沈文渊待她不算差,却也始终把她当伺候人的下人,从未让她有过半分上桌吃饭的体面。地上的瓷片溅到脚边,她下意识弯腰去捡,指尖刚碰到冰凉的碎片,就被沈文渊的笑声打断,整个人愣在原地,眼里满是茫然。 “慌什么,碎碎平安!”沈文渊的笑声爽朗,脸上带着难掩的喜色,目光落在李氏身上,少了往日的疏离。李氏抬头,瞥见管家还站在门口喘气,脸上满是激动,嘴里还在不停念叨:“老爷,真的是大喜!京城来的差官刚到门口,说您的政绩被巡抚大人上奏朝廷,皇上龙颜大悦,封您为五品同知,还赏了恩典,准许您抬举家中侍奉有功的人!”这话一出口,王氏刚到嘴边的斥责硬生生咽了回去,脸上的怒色换成了惊讶,随即又添了几分复杂。李氏听得心头一颤,手里的碎片差点掉在地上,她活了大半辈子,从未听过这样的好事,更没想过这好事会和自己有关。 沈文渊起身走到李氏身边,示意她起身,语气比平时温和了许多:“起来吧,地上的瓷片让下人来收拾。这三十三年,你伺候我和夫人尽心尽力,从没出过差错,当年我在外地任职染了风寒,是你日夜守在床边照料,才捡回一条命,这份情,我记在心里。如今有了朝廷的恩典,也该给你一个体面。”李氏慢慢站起身,腰杆却依旧弯着,不敢直起来,眼里的茫然渐渐多了几分委屈,鼻尖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想起刚抬为通房那年,生过一个女儿,可惜没保住,王氏虽没明着苛责,却也让她禁足了半个月,那段日子,她白天照样伺候人,夜里偷偷抹眼泪,没人过问她的伤痛。这么多年,她吃的是主家剩下的饭菜,穿的是缝缝补补的衣裳,手上布满了冻疮和老茧,都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她从不敢奢求什么,只盼着能安稳过日子,却没想到有一天能和主家一同上桌吃饭。 王氏坐在桌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压下心里的不适,开口道:“既然是朝廷的恩典,也是该的,只是规矩不能乱,往后该伺候的还是要伺候。”沈文渊点点头,拉着李氏走到桌旁,指着一把椅子让她坐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今日就破例一次,往后便让她在桌边伺候,不用再站着了。”李氏迟疑着坐下,浑身僵硬,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桌上的鸡鸭鱼肉冒着热气,香气扑鼻,她却没半点胃口,心里又酸又暖,更多的是不真实。她偷偷看了一眼王氏,王氏脸上没什么表情,却也没再反对,只是偶尔看向她的眼神,依旧带着几分疏离。 吃饭时,沈文渊给她夹了一块鸡肉,李氏连忙起身道谢,手都在发抖。沈文渊笑着让她坐下,感叹道:“当年我不过是个穷书生,多亏了你和夫人陪着我吃苦,如今总算熬出了头。做人不能忘本,你的付出,该有回报。”李氏低着头,小声说:“这都是奴婢该做的,不敢奢求回报。”话虽这么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这么多年的隐忍和委屈,好像在这一刻都有了着落。她慢慢拿起筷子,夹了一口青菜,嚼在嘴里,却觉得比以往吃过的任何东西都香。 饭后,沈文渊让人给李氏准备了一身新衣裳,还吩咐下人收拾出一间单独的屋子给她住。李氏摸着身上崭新的绸缎衣裳,看着收拾干净的屋子,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就算有了体面,她依旧是沈家的下人,地位依旧不能和王氏相比,可这一点点的改变,已经足够让她感激。她想起爹娘当年卖她时的不舍,想起这些年的辛苦,想起那个没保住的女儿,心里百感交集。 1904年的清朝,等级森严,通房丫鬟的地位低下,能得到这样的体面,已是难得。李氏的遭遇,是那个时代无数底层女性的缩影,她们依附于男人生存,一辈子操劳,却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沈文渊的举动,或许有感念旧情的成分,或许也有碍于朝廷恩典的考量,却终究给了李氏一点温暖。那个摔碎的瓷碗,成了李氏人生的转折点,让她在苦日子里看到了一丝光亮。 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命运大多身不由己,李氏用三十三年的隐忍换来了一点体面,已是幸运。可更多的女性,一辈子都在底层挣扎,连这样的幸运都得不到。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被礼教束缚的苦难,终究会被慢慢打破,而每一个在苦难中坚守的人,都值得被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