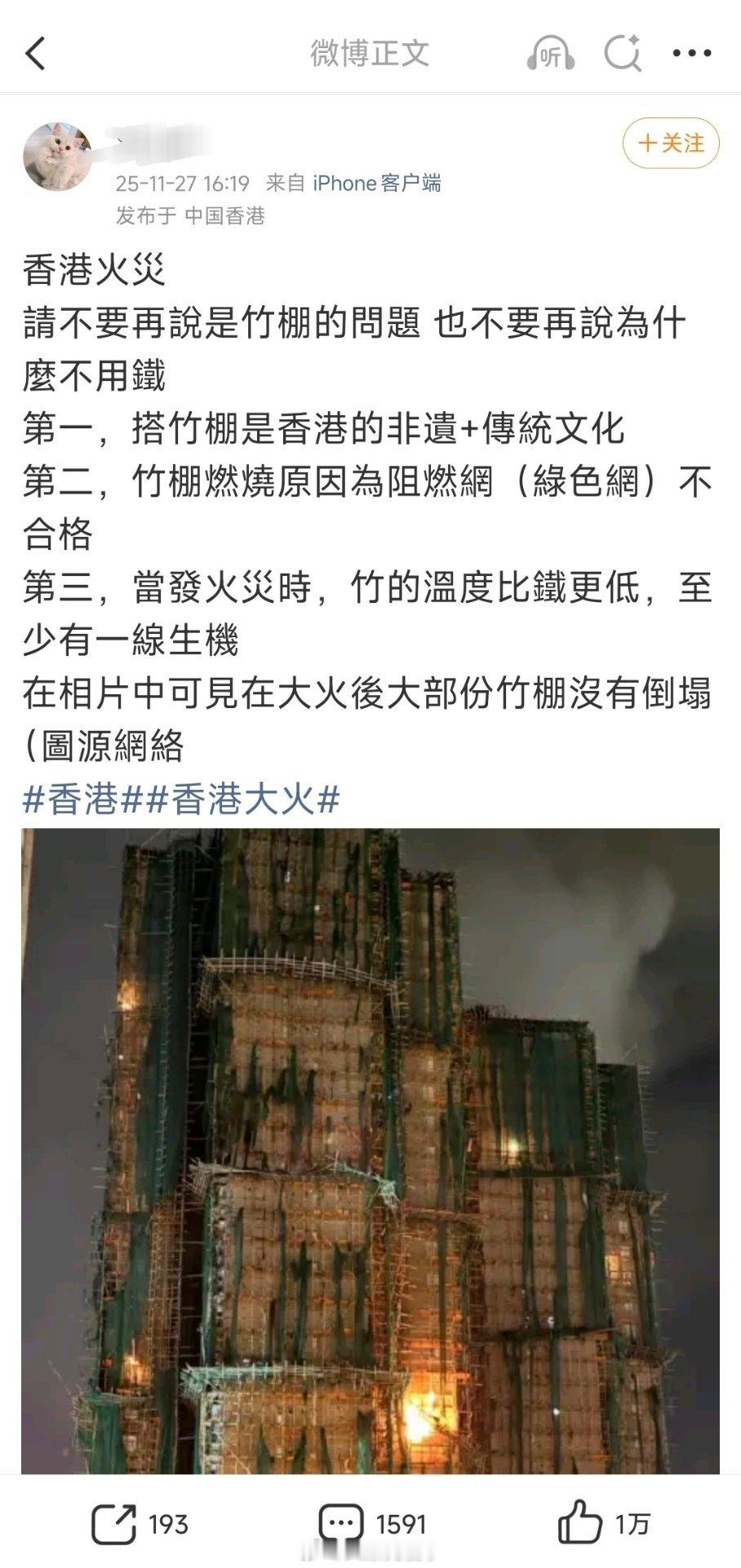上世纪90年代的车间里,焊花味儿还没散尽,一沓X光片在桌上摊开,二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专家围着,手指点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纹路直摇头。 “不合格,200多处裂纹,这喷管废了。” 角落里突然冒出个声音,带着点金属摩擦似的沙哑:“这是假的。” 说话的是高凤林,一个普通焊工,手上还沾着焊锡渣子,指甲缝里嵌着黑灰。 那会儿咱们正搞长征三号甲火箭,那可是“大国重器”,心脏——新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卡了壳。 卡在哪儿?发动机的大喷管焊接。那活儿细得要命,几百根空心管子,每根就比头发丝粗那么一丁点儿,得严丝合缝焊一块儿,焊缝加起来快有一公里长。 好不容易焊出来,拿去照X光,片子上白花花一片裂纹,专家们脸都白了——这要是真裂了,火箭上天就是“空中放烟花”,几亿投入打水漂不说,国家任务都得黄。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有人拍桌子说“必须报废”,有人翻资料说“工艺极限到了”,高凤林蹲在墙角,盯着片子看了半个钟头,突然站起来走到桌子中间。 “我焊的,我知道。”他指着片子上最密的那片白影,“这不是裂纹,是焊料堆积的影子,机器认错了。” 专家们一下子炸了锅,有个戴眼镜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小同志,说话要负责任,X光机是德国进口的,精度0.01毫米。” 高凤林没退让,从口袋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焊枪头:“我练了十五年,手上的感觉比机器准。不信,切开看。” 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切开?那喷管价值连城,切开要是真有裂纹,照样报废,可高凤林就得背上“耽误国家大事”的罪名。 最后还是总工程师拍了板:“剖!出了问题我担着。” 车间里临时搭了个工作台,喷管被固定在架子上,铣刀慢慢切下去,铁屑簌簌往下掉,高凤林站在旁边,手攥得发白,指关节都捏出了红印。 切开,打磨,再放到200倍的显微镜下。 所有专家都凑过去,眼睛瞪得溜圆,连呼吸都憋着。 显微镜下,焊口光滑得像镜子,别说裂纹,连个毛刺都没有。 “真没裂!”有人忍不住喊出声,高凤林腿一软,靠着墙滑坐在地上,后背的工装全湿透了。 后来这喷管成了“功勋喷管”,地面试车一万多秒,愣是没出一点毛病,高凤林的名字也跟着传遍了航天城。 有人说他“运气好”,高凤林听了嘿嘿笑,从工具箱里掏出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那是他当年练手用的,里面盛着水,端着走一公里不洒一滴。 “哪有什么运气?”他摩挲着缸子沿,“吃饭时拿筷子当焊丝,对着空气练送丝;休息时举铁块练臂力,一举就是俩小时;焊枪把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三层,才摸出点‘手感’。” 这“手感”有多准?后来他带徒弟,让闭着眼焊1毫米的缝,徒弟手抖得跟筛糠似的,他拿过焊枪,耳朵听着电弧“滋滋”的声音,手上稳得像长在上面,焊完一量,不多不少,正好1毫米。 再后来,另一个焊工刘红光更神,他焊火箭发动机壳体,有些地方空间太小,焊枪能伸进去,眼睛却看不见——这就得“盲焊”。 焊丝和焊件的距离得控制在1毫米内,差一丝都不行,刘红光闭着眼,光凭手上的触感和电弧的声音变化,就能焊得比机器还匀实。 有次国际焊接大赛,俄罗斯专家围着他看,看他闭着眼焊完一条缝,拿尺子一量,不差0.1毫米,专家们当场掏出相机狂拍,嘴里“哈拉少”不停,觉得这简直是“魔法”。 现在不少企业迷信数据、流程、自动化,觉得机器比人靠谱,这话没错,工业进步离不了这些。 但高凤林总说:“机器是死的,材料是活的,有时候那0.1毫米的偏差,机器读不出来,人的手能摸出来。” 后来有人开天价挖他,北京两套房,工资翻三倍,老婆劝他:“咱儿子结婚正缺房,去呗。” 高凤林蹲在院子里抽烟,烟蒂扔了一地:“诱惑大不大?大,谁不心动?都是凡人。” 但他没走。 再后来,他主焊的发动机把卫星送上天,电视里放发射画面,他蹲在车间门口,看着火箭尾巴拖着光冲上云里,咧着嘴笑,眼泪却顺着皱纹往下淌。 “你看那光,”他指着天上的亮点,“比啥都亮堂。” 现在他还是天天泡在车间,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徒弟问他“啥是工匠”,他拿起焊枪,对着一块钢板比划:“就是把简单的事做一万遍,做到闭着眼都错不了;就是敢跟机器叫板,因为你比机器更懂手里的活儿。” 那天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焊枪头在余晖里闪着光,像一颗没灭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