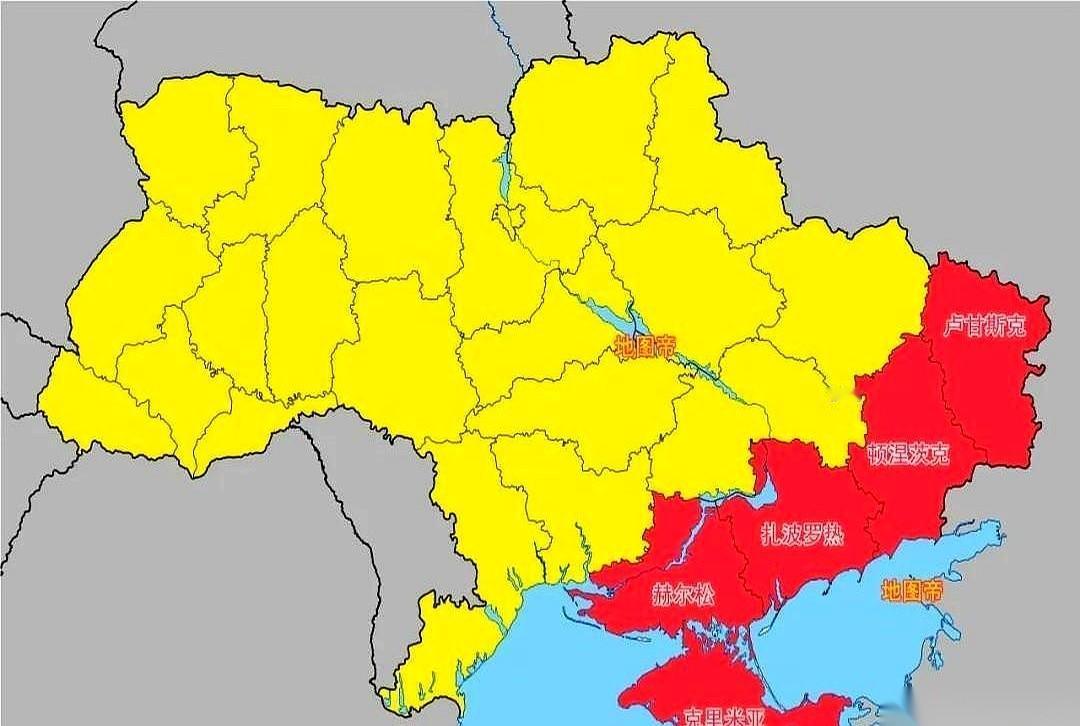1991年秋,北京东四轿子胡同的槐树叶落了一地,杜维善踩着碎叶子站在巷口,抬头看那扇掉了漆的朱漆门。 手里攥着的东西硌得掌心生疼,是张对折的民国地契,黄纸都发脆了,边角磨出毛边,上面“杜月笙名下私产”几个字,还是当年请账房先生写的小楷。 他来这儿,是想把父亲当年给孟小冬置的四合院收回来。 推开吱呀响的院门,院里挤得像个杂货铺,煤棚子搭在石榴树下,晾衣绳从东厢房拉到西厢房,上头挂着蓝布衫子和小孩的虎头鞋。 “你找谁?”西厢房门口蹲个大爷,手里正择菜,抬头眯着眼打量他。 杜维善把地契往石桌上一放,指了指上面的名字:“我是杜月笙的儿子,这院子……” 话没说完,北屋门“哐当”开了,出来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扫了眼地契,鼻子里哼一声:“杜月笙?那是哪年的皇历了?我们在这儿住了快四十年,房梁都是我爹当年换新的。” 院里陆续出来几户人,有抱孩子的大嫂,有拄拐杖的老太太,七嘴八舌的,最后还是那花衬衫男人开口:“要收房也行,我们四家,每家给五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那年北京工人月薪才两百多,五百万跟抢钱似的。 杜维善捏着汗湿的地契去找相关部门,档案柜里翻出的材料让他愣了神:1950年,孟小冬的弟弟孟学科早就把这院子卖给了一家绸缎商,交易用的是金条,白纸黑字的契约,政府还盖了章。 民国地契在新产权证面前,软得像片旧棉絮。 那房子最后拿回来没? 自然是没。 他蹲在胡同口的石阶上抽烟,烟蒂丢了一地,秋风卷着槐树叶往他鞋上撞。 手里的地契被风吹得哗啦响,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杜月笙在上海的公馆里教他写字,砚台里的墨汁映着梁上的燕子窝:“家业不是砖瓦,是让人记着你做过什么。” 回加拿大的飞机上,他把地契夹进了《史记》里,那书还是父亲当年送他的,扉页有行铅笔字:“读史使人明志”。 第二年开春,他拖着个旧皮箱又回了国,直接去了上海博物馆。 开箱的时候,研究员们都围过来看,里面不是金银珠宝,是几排用软纸包着的古钱币,从汉代的半两钱到阿拉伯帝国的银币,最底下那枚萨珊王朝的金币,边缘还有个小缺口——听说是他在伊朗沙漠里用一块馕跟牧民换的。 “这些,捐了。”他说这话时,手还在摩挲那枚缺口金币,指腹蹭过上面的火焰纹样。 往后二十年,他成了个“驼队”,背着帆布包在中亚戈壁上走,骆驼皮水壶磨出毛边,裤脚总沾着沙砾。 七次回国捐赠,最多一回带了800多枚古币,海关申报单上“货物名称”栏写得密密麻麻,工作人员数钱似的点,金属碰撞的声音比算盘珠子还脆。 上海博物馆给他辟了个玻璃柜,灯光打上去,银币上的波斯文看得清清楚楚。 有回学生问他:“杜先生,您跑那么远找这些旧钱,图啥?” 他从抽屉里翻出张照片,是当年北京四合院的老住户寄来的,照片里石榴树开花了,红得像团火,树下几个小孩正追着皮球跑。 “你看,”他指着照片,“那院子住满了人,就没白占着地;这些钱币呢,能让后人知道,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上,也做了几千年的买卖,也交了几千年的朋友。” 去年在多伦多书展,八十多岁的他蹲在地上签售,面前摆着刚出的《丝路货币图考》,封面上印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眼里能看见穿绳的磨损痕迹。 有读者问起北京的四合院,他抬头笑,眼镜滑到鼻尖上,露出的皱纹里还沾着点粉笔灰——刚给大学讲完课。 “那院子啊,”他慢悠悠地说,“我爹买它是为了有个家,现在里头住的都是人家,也是家;我留点古币,是想让后人知道,中国人心里的家,不光是砖瓦搭的,还有条路,从长安到罗马,走了几千年,还在走。” 风从书展的窗户吹进来,翻得书页哗啦响,像那年胡同里的落叶声